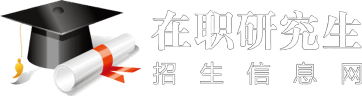學(xué)位證
結(jié)業(yè)證
新聞學(xué):關(guān)注數(shù)字新聞學(xué)的興起與發(fā)展
來源:在職研究生招生信息網(wǎng) 發(fā)布時(shí)間:2022-04-20 17:13:26
近年來,數(shù)字技術(shù)迅猛發(fā)展為新聞業(yè)態(tài)變革提供了條件,數(shù)字生態(tài)下的新聞生產(chǎn)與實(shí)踐模式呈現(xiàn)出不同以往的特征。數(shù)字新聞學(xué)的興起與發(fā)展,為數(shù)字新聞實(shí)踐提供了新的理論解釋范式,也為新聞學(xué)研究提供了全新理論視角。根植于我國數(shù)字新聞的豐富實(shí)踐,深入研究一系列學(xué)科前沿問題,并將經(jīng)驗(yàn)?zāi)殲樾侣剬W(xué)新的理論范式,對(duì)于構(gòu)建中國特色新聞學(xué)學(xué)科體系、學(xué)術(shù)體系、話語體系具有重要意義。
新聞實(shí)踐發(fā)生革命性變化
隨著科技的發(fā)展,學(xué)界關(guān)于數(shù)字新聞學(xué)的討論日益深入。清華大學(xué)新聞與傳播學(xué)院副院長史安斌表示,早期互聯(lián)網(wǎng)的門戶網(wǎng)站、網(wǎng)絡(luò)論壇、即時(shí)通信和搜索引擎等功能與傳統(tǒng)新聞業(yè)相融合,使得當(dāng)前數(shù)字平臺(tái)語境下的新聞生產(chǎn)包含曾經(jīng)界限分明的各類功能,進(jìn)而形成了具有雜糅性和異質(zhì)性的信息環(huán)境。這種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是,一些新元素加入傳統(tǒng)新聞編輯室中,由此帶來的話語權(quán)力關(guān)系改變,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?nèi)藗儗?duì)于傳統(tǒng)新聞業(yè)“采寫編評(píng)播”實(shí)踐路徑的理解。技術(shù)要素可能在其中發(fā)揮更加重要的作用,但同時(shí)會(huì)帶來諸如“信息繭房”和計(jì)算宣傳等一系列新問題。
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新聞首要是一種信息形式,數(shù)字新聞首要是一種信息關(guān)系。深圳大學(xué)傳播學(xué)院教授常江告訴記者,在數(shù)字化時(shí)代,無論新聞的生產(chǎn)、流通還是消費(fèi),都是在一種網(wǎng)絡(luò)化結(jié)構(gòu)中完成的。新聞的角色不再只是“告知”,而是較以往有著更強(qiáng)烈的建立情感連接、塑造情感社群的訴求。當(dāng)下,數(shù)字新聞的生產(chǎn)、流通與消費(fèi)的邊界變得日益模糊。在未來的新聞生態(tài)下,我們看到的是總體的媒介環(huán)境與包括機(jī)構(gòu)、人和技術(shù)在內(nèi)的一切新聞行動(dòng)者之間的互動(dòng)關(guān)系,這種關(guān)系塑造著不同的與新聞相關(guān)的行為邏輯。隨著數(shù)字新聞學(xué)的發(fā)展,學(xué)界需要建立一種新的新聞?wù)J識(shí)論,而不是簡單地提升和優(yōu)化原有的理論。
數(shù)字新聞是數(shù)字條件下的新聞實(shí)踐,數(shù)字化技術(shù)“填平”了信息傳播的介質(zhì)鴻溝。在南京大學(xué)新聞傳播學(xué)院教授王辰瑤看來,數(shù)字媒體的根本變化在于它不是一種新媒體的疊加,而是對(duì)一切傳播符號(hào)進(jìn)行“數(shù)字化”處理后,讓一切媒介“雜糅”起來了。數(shù)字新聞已經(jīng)“溢出”了傳統(tǒng)新聞業(yè)、傳統(tǒng)新聞媒體的范疇。要寬泛地理解“數(shù)字新聞”,理解溢出傳統(tǒng)新聞媒體之后那些現(xiàn)在還不是很清楚的新現(xiàn)象或新問題,如“個(gè)人化新聞”“算法機(jī)制與新聞生產(chǎn)”“新聞報(bào)道與新聞聚合”,以及那些在大眾媒體時(shí)代似乎已經(jīng)弄明白但現(xiàn)在又被“重新問題化”的老問題,如重新理解“新聞?wù)鎸?shí)”問題,甚至重新理解“什么是新聞”。
建立具有解釋力的數(shù)字新聞倫理規(guī)范
在數(shù)字化時(shí)代,以往新聞學(xué)概念體系的解釋力日漸弱化,建立有別于傳統(tǒng)新聞學(xué)的理論和方法體系的需求日趨迫切。
數(shù)字新聞不是傳統(tǒng)新聞學(xué)的延續(xù),而是新聞學(xué)學(xué)科的范式升級(jí)。在常江看來,數(shù)字新聞的意義與20世紀(jì)70年代新聞學(xué)研究的“社會(huì)學(xué)轉(zhuǎn)向”同等重要,也就是說,今天的新聞學(xué)研究應(yīng)當(dāng)努力跳出原有的理論舒適圈,進(jìn)行更加大膽的創(chuàng)新。在數(shù)字時(shí)代,新聞的專業(yè)化或職業(yè)化程度被不斷削弱,新聞在理論上正在成為一種一般性的信息經(jīng)驗(yàn),與人的日常生活融合程度遠(yuǎn)遠(yuǎn)超過以前。這意味著新聞學(xué)體系的發(fā)展要更加鮮明地指向?qū)θ说男袨檫壿嫼蜕罱?jīng)驗(yàn)的解釋,新聞學(xué)需要不斷將自身轉(zhuǎn)化為一套解釋性的知識(shí)體系。
數(shù)字新聞學(xué)和傳統(tǒng)新聞學(xué)在理念上不應(yīng)被割裂開來。史安斌表示,數(shù)字新聞學(xué)研究在理論層面首先要回應(yīng)在當(dāng)前雜糅媒介體系的語境下,多元主體的參與如何改變了傳統(tǒng)新聞業(yè)的生產(chǎn)邏輯這一問題,從而在“實(shí)然”層面解釋數(shù)字新聞對(duì)于傳統(tǒng)新聞業(yè)的沖擊和影響具體是怎樣表現(xiàn)的。這種回應(yīng),能幫助人們理解數(shù)字新聞學(xué)研究的問題意識(shí)從何而來。此外,傳統(tǒng)新聞業(yè)長期以來形成的一整套職業(yè)規(guī)范和價(jià)值理念,不應(yīng)被簡單抹殺。學(xué)者還需要在“應(yīng)然”層面批判性地分析數(shù)字新聞帶來的“信息繭房”和計(jì)算宣傳等問題,并據(jù)此形成一套具有解釋力的數(shù)字新聞倫理規(guī)范,以指導(dǎo)數(shù)字新聞實(shí)踐。
不能因?yàn)椤皞鹘y(tǒng)新聞學(xué)”是“傳統(tǒng)的”就認(rèn)為它注定被淘汰。王辰瑤表示,學(xué)者應(yīng)該理解“傳統(tǒng)新聞學(xué)”概念、原理、規(guī)范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的,對(duì)應(yīng)的是什么傳播條件下的新聞實(shí)踐,然后才能細(xì)致地辨別出“傳統(tǒng)新聞學(xué)”中哪些東西仍然適用,哪些東西需要調(diào)適和揚(yáng)棄。當(dāng)人們面臨“數(shù)字化”語境的結(jié)構(gòu)性變化時(shí),就要細(xì)致考察傳統(tǒng)新聞業(yè)提出的哪些工作方法、職業(yè)觀念的發(fā)生條件已經(jīng)變化,然后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展開討論。人類信息和傳播技術(shù)的空前發(fā)展,實(shí)際上給人們提供了一個(gè)十分難得的“比較”研究契機(jī)。
關(guān)注全球新聞創(chuàng)新和中國數(shù)字新聞實(shí)踐
在經(jīng)典新聞學(xué)體系下,中國本土經(jīng)驗(yàn)和本土理論是較為邊緣化的。常江認(rèn)為,數(shù)字新聞學(xué)的發(fā)展是中國理論和中國話語積極參與甚至在一些領(lǐng)域引領(lǐng)全球前沿理論發(fā)展的一個(gè)巨大契機(jī)。一方面,數(shù)字化給全球新聞業(yè)帶來的變化是一種質(zhì)變,不同國家和文化中的新聞實(shí)踐傳統(tǒng)都遭到了“無差別”的破壞,而全世界所有人都面臨著新的新聞生態(tài)以及這種生態(tài)下的經(jīng)驗(yàn)?zāi)J胶蛡惱砝Ь场_@意味著中國的數(shù)字新聞經(jīng)驗(yàn)具有了更大的可比較性和可通約性,基于經(jīng)驗(yàn)形成的理論也就具有了更大的互鑒可能。另一方面,中國始終是全球數(shù)字化革命的重要引擎,中國的一些觀念和經(jīng)驗(yàn)在全球范圍內(nèi)走在前列。這成為建設(shè)中國特色新聞學(xué)理論的一個(gè)契機(jī),因此中國學(xué)者應(yīng)積極探討如何利用這種實(shí)踐的先發(fā)優(yōu)勢(shì),探索擁有全球性解釋力的理論。
“數(shù)字化”是一次全球性的深刻變革,但不同國家的“數(shù)字化”有不同路徑。在王辰瑤看來,新聞創(chuàng)新必然是一個(gè)全球性現(xiàn)象,但又是一個(gè)高度語境化的問題。目前看來,我國的數(shù)字新聞實(shí)踐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的“制度環(huán)境”。在中國,推動(dòng)媒體深度融合、打造全媒體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、將媒體融合與基層社會(huì)治理相結(jié)合等,都是自上而下的頂層設(shè)計(jì)。與歐美國家以及很多發(fā)展中國家相比,這種上升到國家戰(zhàn)略高度的數(shù)字媒體設(shè)計(jì)方案,是非常獨(dú)特的。中國特色的數(shù)字新聞實(shí)踐經(jīng)驗(yàn)應(yīng)該走到全球新聞創(chuàng)新舞臺(tái)上,并與其他國家特色的數(shù)字新聞實(shí)踐路徑相互借鑒。作為數(shù)字社會(huì)重要信息基礎(chǔ)設(shè)施的各國數(shù)字新聞業(yè),應(yīng)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(chǔ)上“各顯特色”“取長補(bǔ)短”,為構(gòu)建人類命運(yùn)共同體提供可靠且具有建設(shè)性的基于真實(shí)信息的交往基礎(chǔ)。
史安斌表示,對(duì)于中國特色新聞傳播學(xué)學(xué)科體系建設(shè)而言,數(shù)字新聞學(xué)可謂是一個(gè)很好的切入口。一方面,要為處在轉(zhuǎn)型期的新聞業(yè)搭建起一套新的、能夠?yàn)楫?dāng)前數(shù)字新聞實(shí)踐提供解釋的理論范式。另一方面,要讓中國的新聞傳播學(xué)研究擺脫“歐美中心論”的影響,為構(gòu)建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風(fēng)格的話語體系提供廣闊空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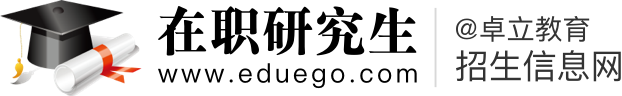

 南昌大學(xué)同等學(xué)力
南昌大學(xué)同等學(xué)力 渤海大學(xué)同等學(xué)力
渤海大學(xué)同等學(xué)力 中國人民大學(xué)同等學(xué)力
中國人民大學(xué)同等學(xué)力 中國政法大學(xué)同等學(xué)力
中國政法大學(xué)同等學(xué)力 南開大學(xué)同等學(xué)力
南開大學(xué)同等學(xué)力